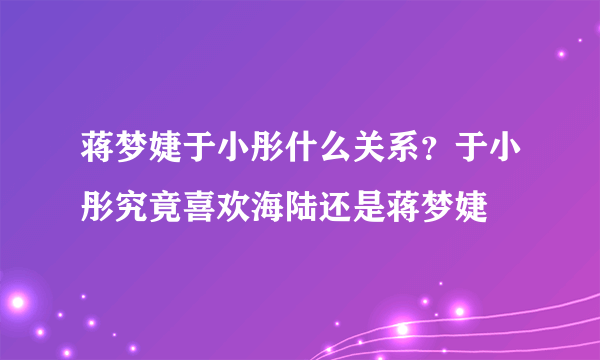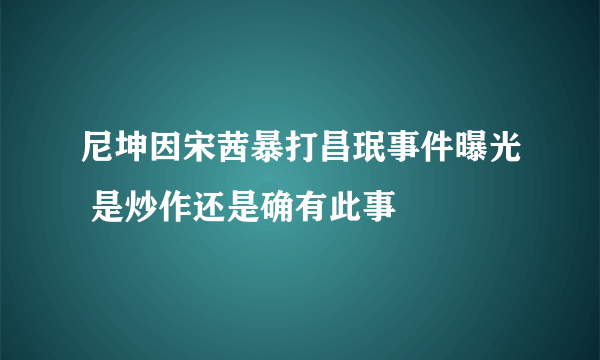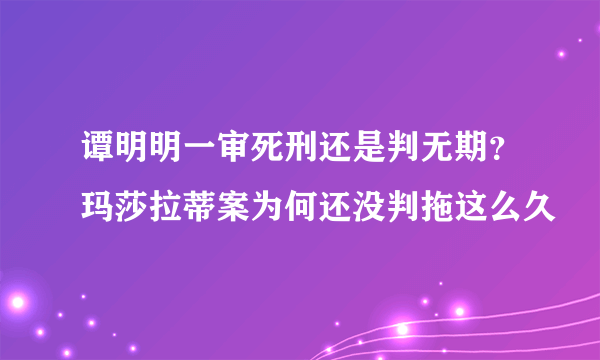那时候天还是蓝的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
那时候天还是蓝的
感悟精选一:
那时候天还是蓝的
那时候天还是蓝的,水也是绿的,河里是能够洗澡的,自来水还是很少的;
那时候庄稼是长在地里的,干活是算工分的,鸡鸭是没禽流感的,猪肉是能够放心吃的;
那时候“耗子”还是怕“猫”的,法庭是讲理的,窗户是没防盗功能的,睡觉是不用担心关门的;
那时候结婚是经人说先谈恋爱的,离婚是要惊动工会领导和居委会大妈的;
那时候姑娘是很害羞的,搞对象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,小伙子还是很含蓄的,丈母娘嫁闺女是不图你房子的;
那时候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,大家的头发都是黑的,学雷锋是不留名的,丢了钱包还是能够找到的;
那时候药是能够治病的,看病是不用塞红包的,医生是救死扶伤的,拍电影是不用陪导演睡觉的;
那时候流氓都是男的, *** 犯是要枪毙的,蹲过号子的是很难找到工作的;
那时候照相是要穿衣服的,欠债是要还的,走亲戚是能够拎只老母鸡的,孩子的父亲也是明确的,(开业贺词)
那时候学校是不图挣钱的, *** 是不能当教授的,上学是自我走路去的,放学是要排队的;
那时候差生是要站黑板的,补课也是是免费的,老师还是不骂人的,打架了老师是要家访的;
那时候男生是短头发的,红领巾是自我洗的,班长是带头干活的,女生被欺负了男生是要出头的;
那时候评三好生是论成绩的,考大学是很难的,受表扬是发练习簿的,处分是记入档案的;
那时候卖狗肉是不能挂羊头的,结婚了是不能泡MM的,打架是有人劝的,兄弟姐妹是能够交心的;
那时候东西是便宜的,买米还是凭票的,当官是为民的,收了贿赂是要蹲大牢的;
那时候人们都是叫“同志”,上街是不用担心飞车抢的,婆媳是天天见面的,老婆还是洗衣服做饭的;
那时候逢年过节街坊邻居亲戚兄弟姐妹是互相窜门的,
那时候人们都在树荫下、街道旁聊天的,
那时候男的就是男的,女的就是女的,(梦见洗头)
那时候RMB不是万能的,
天还是很蓝的……
感悟精选二:
那时,天很蓝?
文·小白
总习惯于一个人望着天空静静的发呆,不知在想些什么,云淡风轻,却是如此的风情,好像空气中都弥漫着这一时节的味道,阳光也是甜的,总钟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小屋内,看窗外风生水起,花儿开了又谢,谢了又来,好像不知疲倦似的,昨夜起风了,花絮散落了一地,把一抹清香带走,把寂寞留在枝头,谁还弯腰拾起风吻过的美丽,夹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中,如今翻开看看,是否还有秋枫漫野的回忆,好像我没有勇气采撷这散落的又一花开,站起身来,静静地走了好久,把一切抛在脑后,只留下斜阳中的一抹红晕,好像一切就这样漫不经心的过去了,而我只是一个过客罢了,背起行囊,拿出纸笔,想记忆起路边的风景,抬起头来,一切早已不见了踪迹,
也许走得太快却忽略了脚下的路,或许当咱们转过身来看一看,错过的风景就好似断章的线把前前后后的身影偶尔的连在了一齐,相遇却是不经意,犹记得那年咱们曾哭过、笑过、幻想着下一个路口,琴声悠悠一齐走过的日子,那么明朗,而如今呢,确实如此的苍白无力,断章的风景依稀模糊了身影,就好想连黄昏都厌倦了云卷风清的日子,悄悄地躲进鸣奏的夜章,暗自沉殇,白天给不了温暖,夜里还是依旧那么寒冷,走了,片刻的眼神还在记忆这以前的热土,泥土中还残留着花的气息,零落尘泥香如故,往事如风、如烟、如雪、似秋、似冬,又是一年情。
走吧,该走的始终要走,谁也留不住,正因远方还有人等你,下雨了,下吧,让一切模糊了、模糊了远方清晰的身影,那好像是你、是我、却是童年。模糊了打伞离去的眼眸,那是谁呢?模糊了秋枫破碎哽咽离散的烟雨,你可知道,那是不舍,正因,春天过去了。当初的我是那样的天真,好想把一切停留在回望你的眼神,当我翻阅著时刻的碎片,掸落缝隙里的尘埃,尘埃易碎,他老了,经不起折腾,哦,当转身一看窗外依旧摇曳的秋千,还有风伴随一季又一季苍老的岁月,那堆得很厚的碎片好像还在默默讲述著身后的故事吧
那时,天还很蓝,当一切成了不经意,这就是过往,看那夕阳慢慢的走进了地平线,好美,以前的风韵还会回来的,我似乎能够看到旭日的晨曦还在陪她一分、一秒,等她一天、一年,甚至是更长。正因我知道他舍不得这原野的枫,更多的是自由,离不开漫山的绚烂,当然,还有多情的黄昏呢,那些当初的一抹笑呢,晕开了城外,或许冷漠、或许不再、又或许是另一番景象了吧,破碎的流年让咱们慢慢长大,不觉间,当咱们采撷花香时思考她会不会痛苦一样,把老的、过往的破碎残落了一地,却遗忘了沐浴新生的一束阳光,咱们不也一样吗?当咱们走在以前领悟生活过的校园,我想,留给咱们的只能是那份沉甸甸的记忆啊,以前的你,以前的我,你在哪里?我又在哪里?只是还记得,那年,天还很蓝
把窗帘拉开,天还很蓝(高尔基的名言)
风还在徘徊,也许怕寂寞
摘一束花开
一片、两片、撒满
你走过的窗台
我在远方还看你
雨还笑我的发呆
把花絮放在口袋
正因
我还会来
感悟精选三:
那时候天总是很蓝
那时候我总在想未来的自我是个什么样貌,有时想着想着就好累,还好有真子,她冲我笑笑,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,她说,我拉着你,慢慢溜,没事的。
是深秋吧,阳光懒洋洋的,天空高高地挂著,大风吹,大风吹,爆米花儿好美。
真子不叫真子,叫徐佳贞子,我一向是误写,却也是刻意地写作真子,正因她率真的性格,和似乎没有被污染的纯净的微笑。
咱们的父亲是同事。有时我写字,趴在高三年级组父亲靠窗的办公桌子上,一遍一遍写着几行年代久远的诗,真子就把我藏青色的帆布包翻的乱七八糟,有满分的试卷,有打着红叉的数学作业本,有封面花花绿绿的漫画,也有一颗一颗晶晶亮的彩虹糖,总之真子是全部要看的,我就任由她了。
她跟许多人一样,爱读我软抄上的文字,有时自我写,有时抄著戴望舒、席慕容的的诗,有时是几笔线条简单的画,真子仔细地翻看,就突然抬头问我,所有的完美都会消失吗?
都会消逝吗?
那之后,日子一样往后翻著书页,没有停止的样貌。
我和真子半年都没有见面。然后的一个初春,我脱了厚外套和许垚一齐去篮球场上扔球,看到真子背了一个大大的Nike包,白色的大勾把我的眼睛都刺痛了。她站在门口那边,剪了干净的短发,依然漆黑明亮的眼神,只是,只是换了淡定持久的微笑,有些让我不习惯了。
她的父母离异了,我本不想知道的,以至于我对感情有一段时刻产生了仇恨。我抚真子的短发,神情有些恍惚,她只小我一岁,却要长得比我还高。
天还是蓝的,幸好她也是蓝的。依然蓝得没有一丝杂色。
真子的假期一向和我在一齐,那是两年前的寒假,没有人陪她,只有我牵着她的手,去吃牛杂火锅,两个人在众人的微笑中挥舞著筷子,为一切疯狂。
安静的时候去楼顶,整夜坐着看星。真子总有那么多话要跟我说,说到冰淇淋哭花了脸,说到汽水停止了冒泡,说到东方一片金碧辉煌。
真子最后一次来找我,是借一本书。很多很多的书把书架都要挤爆了,她只默默地抽出一本张悦然的《樱桃之远》。我问她,你能读懂么?
真子笑得灿烂,恩,我只小你一岁,明年就和你一般大了!
我眯着眼睛远远地望着她,上车,招手。
你必须要写字,一向写,不好停下来,还要 *** 子哦——
这是我听到的真子很用力呼喊的一句话,似乎用尽了毕生的气力,似乎也是心底的声音。
雪落寞地飘了下来,天空一片苍灰。我转过身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想起那时候,天总是很蓝。
很蓝很蓝。
不知道早上学是该庆幸还是就应去撞墙,总之我初二那时侯感觉挺悲惨,正因每次放学都会看到很多楼上楼下的小孩在操场上玩,尤其是徐垚,明明跟我同岁,顶着一张娃娃脸跟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。
还好初二的时候有假能够放,作业也容易,徐垚就拿石子扔我的窗子,等我探出脑袋,就看见他在二楼的阳台上用无比挑衅的口气冲我叫,下来啊,咱们来挑拳皇。
游戏机这种东西,用脚指头想也知道我连按什么键都搞不清楚,但是我常常走运,不是吃了什么好东西就是把徐垚控制的大BOSS主角逼到墙角一向用扫螳腿赖赢,胜的几率超高。
和徐垚合作最默契的是很可爱的过关游戏——《雪人兄弟》,已经到了无敌的水平:咱们摸透了怎样发雪球能够有东西吃,吃什么能够加分加命,什么时候怪物变形了该逃跑,还有过大关后的摇奖机怎样摇能够停在小雪人上……尽管是这样,咱们还是没能透过全部关卡,正因咱们总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抢夺一瓶药水,而忘了打那些傻傻的小怪物。
等FC玩够了,玩GB、GBA、SFC,之后是PC,告别了单机游戏后,那些经典的卡、碟也随2003年的夏天一齐被锁进了抽屉。
之后徐垚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,我的功课也越来越重到无法呼吸。那段时刻,总是觉得周遭的世界像个大火炉,我被扔在其中炼提,不断挣扎、辗转,生活失去了纯净的颜色,褪了单纯的完美,就要把我吞噬。
深秋亦或严冬,总之是在一个冰凉的季节,我斜背着红书包交叉着手臂慢慢走到教室去,雾气浓重得把发梢也染湿了。我抬手去撩散在前额的又短又碎的头发,就突然看到徐垚站在路灯柱子旁边,熟悉的胖乎乎的脸,整齐的牙齿,只乐呵呵地看着我笑。
我当时鼻子一酸,冲上去就是一拳,叫嚷着,欠姐姐的一个木叶护额不打算还了吗?
徐垚蛮不服气地努努嘴,说,只但是大我一星期而已,零舍一入,咱们是一样大的!我从广州给你带了质量最优的——卷轴!抱歉,没有护额啦!
我只气得吐泡泡,原来去了广州。可却忘了问他去的原因,正因中考彼时已经塞满了我的脑子。
徐垚又留了一级,之后我才知道。他在广州就留了一级,此刻才上初二,留着李洛克式的头发乖得可爱,谁都看不出他和我一样大。
中考完后,和徐垚、真子三人每一天晚上在办公室免费上网,被徐垚教会了玩《飞飞》。他本来说了很大一堆网络游戏像什么梦幻什么冒险之类的,我只说有什么个性的,他答有,《飞飞》,唯一一款会飞的网络游戏,能够飞上近乎真实的天空了。
于是我砍著砍著就钟爱拖着鼠标右键转换视角,抬头看天空中那些骑着扫帚飞的魔法师,还有洁白的云朵,天黑时绚烂的星光,漂亮得能够让人忘却所有的苦痛悲伤。
终是没有飞起来,正因很快我又被卷入琐碎中了,为不知道的目的忙碌著,奔走着;我不知道自我要的是什么,却又不得不一向不停地往前走,这多可悲。
假期结束了,我背着有旅行包那么大的书包去上学,把所有陈旧的腐烂的发臭的都抛在那里,笑得张狂极了,说,徐垚,你一个人在那里郁闷死吧,我走啦。
而一个月不到,我却快要郁闷得要死掉了,而又不止是郁闷。是什么?天晓得。
天不会晓得,它蓝得那么纯净,不染一丝尘世的污浊,也不懂人类复杂丑恶的心。它总是那么蓝那么蓝,会懂得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