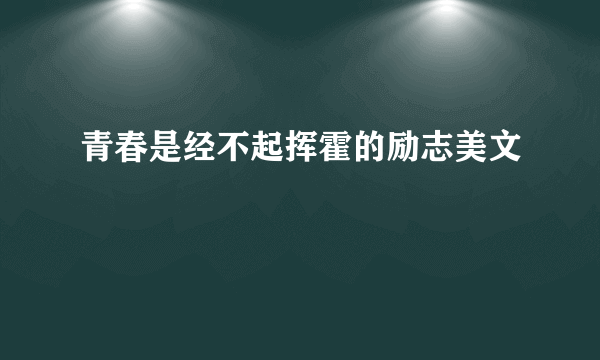大尺寸的小黄说说1000字美文?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
一株行走的草一株行走的草 敕勒川,阴山下, 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 天苍苍,野茫茫, 风吹草低见牛羊。 我来到广阔的草原上,被细微的声音吸引。 那是自草原底层所发出的,牧草舒络筋骨的声音;也是被风吹袭时,草尖与游云相互拥舞的声音。那是人声交错的世界里听不到的微语,人的眼眸与耳识总是停伫在尘世的荣华上,遗忘了草原上有更深奥的交谈。 我逐渐明了,其实人世的生灭故事早已蕴涵在大自然的荣枯里,默默地对人们展示这一切,预告生生不息,也提挈流水落花。人必须穷尽一生之精神才能彻悟,但对这草原上的每一棵草而言,春萌秋萎,即具足一生。人没有理由夸示自己生命的长度,人不如一株草,无所求地萌发,无所怨悔地凋萎,吮吸一株草该吮吸的水分与阳光,占一株草该占的土地,尽它该尽的责任,而后化泥,成全明年春天将萌生的草芽。 众草皆如此,才有草原。 我不断追寻,哪里能让我更沉稳,哪里可以教我更流畅;在熙扰的世间,却不断失望。才知道我所企盼的,众山众水早已时时对我招引,只是我眼拙了。山的沉稳,成就了水的流畅,水的宽宏大量,哺育了平野人家、草原牛羊。 如果田舍旁的稻花曾经纾解我的心,不仅是勤奋的庄稼人让它们如此,更是平野与流水让它们如此。如果,深山里的松涛曾经安慰我,那是山的胸襟让它如此。如果桃花的开落曾经换来我的咏叹,我必须感恩,是山、水、花、鸟共同完成的伦理,替我解去身上的捆绳。 我不曾看到一座单独的山,山的族群合力镇住大地;也不曾看到一条孤单的河,水的千手千足皆要求会合。不曾有过不凋萎的桃花,它们恪守生灭的理则,让四季与土地完成故事。 荣,是本分的;枯,也是本分。 在我眼前的草原,无疑地也是天地伦常的一部分。吸引我的这一幅和谐,乃是天无心地苍茫着,山无心地盘坐着,草原无心地拂动着,牛羊无心地啮食着,而我无心地观照着。 此时的我,既是山里的一块岩,也是天上游动的云;是草的半茎,也是牛羊身上的汗毛。 人不能自外于山水,当我再次启程,我是一株行走的草,替仍旧耽溺在红尘里的我,招魂。你是一只蜻蜓,点过我的湖心。然后我的记忆便以涟漪作裙,连寂寞都细绣缀锦,至此,我青春绮丽。秋风将冷寂大把大把地撒向大地,艳阳下便有了声声低吟。我侧耳倾听,可是风里所有关于你的消息都叫静谧,每一次的错过都叫忘记。我不该怪你,没有把叶芝深情的诗读给我听,因为我们没有正面的相遇,只是你太累了时恰巧路过我的湖心;我不该怪你,以一枚梧桐树叶凝滞我的呼吸,因为你内心的锚过于沉重,你不期待再一次冒险的航行;我不该怪你,用一瞬间的相思换取我永世的铭记,因为你拥有一双飞翔的翅膀,注定要离我远行。你是一只蜻蜓,点过我的湖心。然后,羽翼颤动的声响,渐渐远离我惶恐不安的心情。可是你的离去却没有让我恢复平静,我因此陷入忧伤的旋涡。那波纹优美的线条汇成阻力,围困了我的心。你把我从梦境深处唤醒,却只为告诉我,你要借着风筝远离六月的雨,而我却只能留在原地。我把我们的秘密全部尘封于树林寄给秋季。我躲在秋的衣襟里回想当时的心情----------那是一个永远的蜻蜓梦,似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清醒。你是一只蜻蜓,点过我的湖心。我错把结局当成了开始,我始终无法相信,与你的缘份就这样随荡开的波纹渐次散开。你冲破我的视线,消失在天边湛蓝的颜色里。于是我知道。你不再是蜻蜓,而我不再有湖心。名 家 美 文1、一墨乌镇 彭学明说乌镇是一墨乌镇,是因为乌镇的底色是墨色的。淡淡的墨色,让乌镇显得格外古朴。乌镇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,几千年如一日地站着、坐着或者蹲着,既老成持重,又沉稳肃穆,当然也很沧桑和简朴。一件粗布衣穿了3000年,一件灰色裤穿了3000年,一件褐色被也盖了3000年。3000年不浓妆艳抹,3000年不花枝招展,3000年一种本色,难啦!然而正是这3000年不变的颜色和本色,才完美了乌镇成就了乌镇,才让乌镇以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穿越了时空,扬名中外。乌镇是老,但老得周正老得硬朗,老得神清气爽。就像酒,越老越香。斑斑驳驳的墙壁,只是它风霜岁月的一层老茧。墙顶的几把荒草,只是它仙风道骨的几缕胡须。而那些浅浅淡淡的青苔,则是它人生磨难出的一点点老年斑。石板铺就的街巷,平平仄仄地穿行在乌镇的每一个角落,或长,或短,或窄,或宽,或直,或弯。是乌镇斩不断的根,割不了的筋。没了这每一条街巷,乌镇就没了章法,乱了方寸,乌镇就成了一潭死水、一盘死棋,乌镇的人就走不出自家的屋檐,只能坐井观天。上了年纪的人,有许多上了年纪的记忆,花儿正开的人,也有许多难忘的回忆。不管是谁,只要走进乌镇的这些小街小巷,只要踏响每一块发亮的青石板,就会唤醒许多尘封的故事,就会生出许多深长的遐想,就会不由自主地披满一身古色古香。不要说戴望舒的古巷和丁香,更不要说跟戴望舒诗句一样的姑娘。乌镇有的是江南柔情的雨丝,有的是雨丝下打伞荷笠的姑娘。因为乌镇本身就是一束江南的丁香。你运气正好,对面走来了一个江南的女子,背面也走来了一个江南的女子,两个女子都笑靥抿抿,两个女子都鲜若桃花,两个女子的秋波都与你在这里狭路相逢,你选择哪一个?哪一道秋波更能打湿你爱情的梦?哪一泓秋水更能漫进你温柔的梦乡?如果为难,那就别急,先跟着她们走走,往她们的家走,往乌镇的深处走,也许答案就有了。进得家来,一声声吴越软语会给你让座。院子虽有大小,却是一个风格。临街的墙是木板,背街的墙是火砖。临街的一面都打开一扇窗口,或开一个店铺,或看过往的行人。院子里,青青的平砖一席铺地,有水阁,有绣楼,有回廊,有精雕细刻的门窗和木床。那门窗和木床真漂亮,花在上面开,鸟在上面叫,蝶在上面舞,鱼在上面游,还有蔬菜还有庄稼还有家禽,都在上面鲜活地飞翔和成长,也许他们一辈子就是为了一栋好房和一架好床,所以他们才费尽心思把智慧、荣耀和一生的梦想都刻在了上面,留给了后人。那些大户人家,更是以几进几出的宫殿气派,不张不扬,却大手大笔的,展示着自己的荣华与富贵。无论荣华富贵还是淡泊清贫,乌镇都是含蓄而内敛的。就说徐家厅、朱家厅和张家厅,里面那么富丽堂皇那么气派宏大,外面却与贫民百姓一样普通,有如小家,亦如碧玉,与整个乌镇浑然一体。由此,不管怎么看,乌镇就都有几分平淡几分儒雅几分绅士。打铁的,染布的,唱戏的,经商的,穿官袍的,都在不经意间透着一种平和、一种文气。不知是家家都种着花养着鸟,还是个个都识点文断点字有点见识,时光和岁月就是遮不住乌镇人的淡淡书香。是什么呢?或许是家家门前挂着的那盏红色灯笼,或许是条条巷子飘出的那段印花染布,或许是满镇子飘着的那比歌声还柔软的声声吴语。染完一段花布,织完一个竹筐,或者烧好一缸老酒,乌镇人就三三两两出来,或摇着蒲扇斜依在自家的门槛边,或端着茶杯来到街头的戏楼茶院,听风说雨,摆古论今。一个个故事,一则则新闻,还有一段段传奇、一桩桩姻缘,就这样把乌镇点染得更加文弱和温情。茅盾先生的《子夜》、《林家铺子》、《春蚕》、《秋收》和《残冬》等巨著也许就是这么来的,他笔下的那些人物,也许就是这些乡亲。是的,乌镇出了不少人物,但有一个茅盾就够了!一个茅盾,就足以让乌镇骄傲,足以把太多的人和城镇比下去了其实,更精彩的是在水上。乌镇的水是浑浊的,远不及我故乡湘西的水清澈甘甜,但乌镇的水是为乌镇而生的。没有乌镇就没有这条蜿蜒迤逦的水巷,没有这一条蜿蜒迤逦的水巷就没有水,没有水,乌镇就没了水色没了灵气没了生命没了灵魂。之所以说乌镇的水是为乌镇而生的,因为乌镇的河是人工的,这运河就是因为乌镇而来这里安家落户的。如果不是为了与乌镇结一门金玉良缘,这运河就不会绕这么远的路,就不会流到这里与乌镇朝夕相处、唇齿相依。所以乌镇与水的关系,是血与水的关系,血浓于水,血也融于水。这条飘飞的水巷,是乌镇的血脉,软软的脉管上,是乌镇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节。租一条蚱蜢舟,我们就驶进乌镇的水墨画里了。悠悠的水巷,像一支写意的工笔,轻描淡写地描摹着两岸,勾勒出两条笔直的风景线。黑瓦白墙的民居,仪态万方地闪立在两边,一半住在岸上,一半跳进水里,它们像一群淘气的孩子,把脚伸进水里,把手也伸进水里,戏弄一河鱼虾。虽然它们没有我湘西吊脚楼的气势和高大,但却小巧精致,异曲同工。水阁的窗口,往往会探出一盏女儿的脸,那不是茅盾笔下的淑女,就是我们江南的表妹,好看,好看,好美,好美。于是你觉得一河的风景都被这女儿的脸照亮了,一河的水阁都是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了。本来也是这样,你看,在那岸边的每一座河埠旁,在河埠的每一条帮岸上,在帮岸的每一条廊棚里,在廊棚的每一个美人靠里,你都会看到一个个洗衣淘米的表妹,一个个挑花绣朵的表妹,一个个等待爱情的表妹。美人靠是什么?美人靠是水乡女儿的专用工具,在临河的每一个廊棚里。不管是男人女人,你都靠一靠吧。靠一靠,你就是美女了;靠一靠,你就有美人了。坐在船上,看着风景,想着美人,再品一品乌镇男人用白水白面白米酿制的“三道白”酒,品品乌镇女人手擀的姑嫂饼,乌镇的滋味就全了,你就品不尽想不完,就乐不思蜀、游而忘归了。那么,留下来,你就会是茅盾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,是千年乌镇的一个情节和段落。(选自《经典美文》2008年第11期)3、郁孤台之魂 徐南铁我与辛弃疾在郁孤台上相会。 八百年的时光衔枚而走,郁孤台几番修修废废,辛弃疾凭栏远眺的凝重身影却在台上徘徊。 你还在俯望江水吗?这江当然不是八百年前的江。八百年前,金兵入侵,生灵涂炭。你叹息那清清的江水中有多少行人泪。如今,废城墙建起了一座华丽的人行桥,桥上行人不断,桥下木船相连。 你还在倾听对岸山中的鹧鸪声吗?对岸的鹧鸪曾经为你的壮志抱屈,与你“天凉好个秋”的心曲唱和。今天,你的鹧鸪已飞入历史的深处。对岸陈列的是工厂、居民。鹧鸪的子孙们只在更远的山林中吟哦古调。 幼时就读过你的“郁孤台下清江水”。那时住在赣州,却不知这郁孤台就在赣州的西北角。乃至知道了城内叫田螺岭的高阜就是你“西北望长安”的高台,我急匆匆兴冲冲地骑着车奔向那里,想依着你的英魂去领略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的沉郁、苍凉以及辽邈的历史感。没想到红漆肃落的院门被一把铁锁紧扣。抬眼望去,郁孤台下一派败落不堪的风雨之貌,灰冷、凋敝,连板壁也不全。只有晾在台上的几件艳丽的衣服才见出一分亮色。但是,在蓝色天幕的衬托下,郁孤台的飞檐高高翘起,依然孤傲、挺拔、风骨凛然…… 今天,我们终于在郁孤台上相会了! 今天的郁孤台披红点翠,焕然一新,好一副西装的雍容贵态。我想信,作为一个“横绝六合,扫空万里”的词人,你不会为一座郁孤台的兴衰慨叹。你的身影不是因台的兴衰而兴衰的。 二层的郁孤台高不过15米,但因建在高处,赣州尽收眼底。赣州不居交通要冲,除了当地的文人墨客偶尔雅集,郁孤台游人不多。这更好,我可以静心同钟爱的词人一起面对这无限关山无限江天,让无限思绪扑面而来。 我问辛弃疾,在郁孤台一千多年的历史中,它接受过那样多的咏唱,苏东坡、文天祥、戴复古、李梦阳……都是文坛巨子,为什么只有你的一首《菩萨蛮》成为千古绝唱? 辛弃疾不语。我久久凝望着他极目天外的侧影,那非常熟稔的神情渐次幻化为屈原、杜甫、白居易,陆游、龚自珍……我猛然明白了!我总是的答案是:贯穿着中华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辛弃疾词中强烈地闪光。 “可怜无数山”的襟怀,“江晚正愁予”的情愫,不就是中华文化脉搏上激起的音符? 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江风中猎猎作响。人去,这种精神不去;台颓,这种精神不颓。即使滔滔江水干了,这种精神也将奔流息地传衍…… 辛弃疾依然徘徊在郁孤台上。我走下台来,久久地回望郁孤台。或许,历代人民屡屡修复它正是为了辛词中的一片丹红? 郁孤台郁结着民族魂!